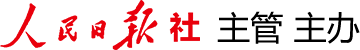亲历者说||林水俊:最早的汽车试验场是这样建成的

林水俊,印尼归侨,祖籍福建省龙海县。
1928年11月,林水俊出生在印尼爪哇岛文池兰镇,1950年7月乘太古轮船公司的岳州号回国。同年考取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53年毕业被分到一汽。
在为一汽效力41年间,他在生产科做过技术员、计划员,在设计处担任过工程师、道路试验室副主任和主任,期间被下放到总装配分厂劳动两年。
1980年,林水俊任长春汽车研究所整车研究室主任。1982年后,历任汽车研究所副所长、海南汽车试验站站长、中国汽车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1986年任汽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1993年底退休。可以说,他这一生都没离开过整车试验。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林水俊主要主持三项与试验室相关工作:一是长春汽车试验场的建设;二是海南湿热带汽车试验场的建设;三是建设中国汽车质量检测中心。
2015年7月11日,87岁的林水俊在位于长春的花园酒店接受本次访谈,为我们还原如何建成中国最早试验场的坎坷经历。
以下为长篇访谈节录。

踏上归国路
我祖籍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1928年11月,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爪哇岛文池兰镇。小学和中学都在华侨学校念书,因此一直是念“中国书”。
学校有外语课程,所以当地话我会讲,英语也会讲。印尼以前是荷兰的殖民地,我也大致了解一些荷兰单词。
1950年我决定回中国。为什么?我对中国历史非常关心。不夸张地说,我学到的历史知识和所了解的事情,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主要得益于马来西亚和印尼当地的华侨报纸以及一些中国历史演义和书籍。
年轻时我最恨英国人和日本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首先侵略中国,其次是日本。当时殖民地的人都怕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是“东亚病夫”。我们这些海外华侨被认为是海外孤儿,所以都希望中国强大,这样在国外才有社会地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多华侨,包括第二代华侨和一些青年学生都先后回国。当年我18岁,很羡慕那些能回国的人。但后来回国同学写信讲,他们在国内很失望。抗战虽然胜利,国民党却没感觉到我们是战胜国,美国人仍在中国作威作福,大家都感到很彷徨。
战争年代,人们颠覆流离。从1941年底日本占领印尼到1948年,因没生意可做,家庭破产,我跟父母分散了六七年。日本投降后,印尼要独立,又跟荷兰打仗,所以生活极其不安定。
上大学时我年龄偏大,大多数同学出生在1931年前后,比我晚三四年。其实我入学很早,中间还跳过两次级。到1948年才插班念高二年级,1950年毕业,正赶上国内解放战争。为什么抗战胜利了,又要打内战,很多在国外的人都不理解。
有件事情使我们下定决心要回国。解放军打渡江战役时,两艘英国军舰帮国民党,却被共产党的大炮打跑。这在国外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用中国武器把外国军舰打跑,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家都非常振奋。
1950年7月12日,我们79名学生乘坐太古公司的轮船岳州号离开雅加达海港,7月30日抵达天津港,前后共18天。

我们坐船直接到达天津,有一张华侨中学生的合影照片,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时任天津市长的黄敬接见并亲自宴情我们。我们一行人大约18、19岁,还比较幼稚,受到(黄敬)市长出面接待并宴请真受宠若惊,感到非常温暖。
事后听黄敬市长讲,当时回国学生很多,我们是第一批有组织回国的学生。这件事惊动了国内外,我们的船要经过台湾,国民党想把船扣留在台湾。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指示黄敬市长: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告诉太古轮船公司,必须保证学生安全抵达天津港,否则一切后果太古轮船公司承担。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清楚,我们的船到底是经过台湾海峡,还是绕过台湾海峡回国的?
我还记得黄敬市长跟我们开玩笑,他说他会讲印尼话,但他把“猪BABI”说成了“仆人BABU”,引得大家大笑。
我们在天津待了两天,8月1日参加建军节。天气特别热,我们都穿着短装,受邀坐在主席台上。8月2日我们到北京,中央侨委安排我们住在东城区王大人胡同。
8月5日,我们在北京参加高考,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只能凭借原来基础参加考试。除我们外,还有从香港到北京的一批华侨学生,他们来自马来西亚、印尼、香港和泰国。我们两班人马在北京会师,200多人参加北京地区统考。
我的同班同学基本都考上了大学,考上清华大学有十来人,占一半左右,我也在其中。那时候优待华侨学生,只要通过录取分数线就优先录取。考试科目包括英语、语文、政治、物理、化学和数学六门。进清华大学后还要面试,进一步了解情况再调整。
在清华大学
我考取的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语文、英语和政治三科基本满分,但数学、物理和化学分数较低,只有60分左右。当时系主任是庄前鼎,他是清华大学机械系元老。
清华大学是花园式学校,没有高楼大厦,基本是低层教室和宿舍,树木很多。有一次气象台开放,我到顶上去看,大学里绿树覆盖,中间有些红瓦,那是教授们的宿舍。还有小河流水,特别漂亮,确实是读书的好地方。
清华大学很重视实际教育,不管学什么,都要多实习,多接触,多动手。1952年8月,我们到天津修配厂实习,主要看他们怎么铸造发动机最难的缸体,跟他们学习修配厂怎么造发动机。
清华大学管理严格,如果有两门功课不及格,或者体育不及格就不能毕业。大一时我数学不及格,如果还有一科不及格就很危险。同宿舍因生病留级的同学在暑假帮我补习,补考时我得了满分,顺利过关。
体育方面除羽毛球外,其他田径类项目我都不行,这方面清华大学培养了我。比如跑步,3000米14分钟及格,起初我1000米都跑不到,后来坚持练习,最终以12分钟跑完,拿到优秀。
还有单杠,起初我最多做三四下,勤练习后能做到十几下。再比如爬绳,三米多高的绳子,人家要用脚帮着,我不用脚就能直接爬上去。体育劳卫制成绩我得了优秀。
机械工程系有80多人,从大二开始分专业,有汽车专业、热力机械专业、精密仪器专业、铸锻专业和机械制造专业。我选了汽车专业,人数最多,有30多人。
1950年8月我考入清华大学,后来通知我们提前一年毕业,参加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听到消息后大学里热闹非凡。清华大学政治风气、体育风气都相当浓厚。但另一方面,大家也有些担心,因为只学了3年,参加工作后到底能不能跟上,心情有些紧张矛盾。
校长蒋南翔做过几次报告勉励我们。毕业典礼会上,他的报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看一个人政治性强不强,要看能不能适应所处的环境。人应该去适应环境,而不是让环境来适应你。只有先适应环境,才有可能想法改造环境。
二是,学校学得的知识,只是基础,到了工作岗位必须继续学习。要谦虚地向有经验的学,向工人师傅学,向周围人学,才能学到真知识。
三是,开始工作不懂不要紧,加紧学习就是。共产党在根据地没有火车,有了火车不会开也不会管理,好像赶马车一样去开火车,后来不也管得很好吗?
四是,要德才兼备,还要注意锻炼身体,要能为党为国家工作五十年。
我们这些毕业生,被集中起来突击学习俄文。清华大学编的教材,目标是一个月会看俄文书。这一个月里,我们就专门学俄文,背单词,背文法,天天都背。俄文文法比较规矩,我们通过查字典基本能弄懂俄文。
到一汽
毕业分配时,一汽建设需要人,三分之一同学被分到一汽,三分之一同学留校,还有三分之一同学被分到全国各地。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参与者,我们感到非常光荣。
从清华大学分到一汽有19人,其中2人搞土木,1人搞电机,十五六人搞汽车。分到一汽正合我意。我在北京待过,所以到东北也不怕冷,不像那些从南方来的同学。
我以为一汽应该有巍峨的建筑,哪知报到时大失所望,这里只是一片荒地。除几栋日伪军留下的建筑物外,什么都没有。到工地去参观,只看到建筑五师的劳动大军在作业。但作为我国第一座汽车厂的第一批技术员,我心里仍然感到兴奋与自豪。
到一汽再分配,我被分到生产部门,科长是支德瑜,他给大家讲,生产科的任务就是搞生产准备,翻译从苏联运过来的资料,包括工艺路线等。我们学过俄文的就直接工作。接着又被分到生产准备办公室,由一汽副厂长孟少农直接领导。
我在生产准备办公室干了3个多月,这期间对汽车厂整体了解较多。比如这个厂由多少个部门组成,包括前方厂和后方厂,主生产车间和辅助生产车间等,这都是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
长春冬天很冷,工厂里铁路建起来后,哪个工厂要施工,就用火车头当锅炉房,用火车的蒸气来取暖,因此冬天也不停工。
1956年工厂三年建成,这要感谢苏联专家。生产过程中,苏联派来技术工人,基本是一对一指导。我们照搬苏联技术,开始50%毛坯铸件从苏联运过来, 1957年后才能自己生产。
生产准备办公室后来被撤销,成立生产处。我在生产处担任计划员、小组长,这期间学到汽车厂如何编排计划和组织生产。概括起来就是,既知道了汽车厂的组成,也知道汽车如何一步步生产出来。
黄敬当一机部部长后,提出一汽不仅要生产载重车,还要生产更多汽车品牌,如军用越野车和轿车。汽车厂要扩大生产,需要更多技术人才搞设计和制造,一汽也提出要从外面招人。趁这个机会,我要求到设计处。
但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画图,我喜欢和整车打交道,因此要求能去试验室工作,而试验室也的确需要人,我就被分到汽车道路试验室。从此后,我再没离开过整车试验工作。
汽车道路试验室隶属于试验车间。当时我刚结婚,调令下来后,晚3天才去报到。试验车间主任是何赐文,后来到汽车局当副总工程师。何对我们要求很高,我因此受到批评。
道路试验室下面分为解放、轿车和越野车三个小组,我被安排在轿车组。试验室大都是非党员人士,科长也是非党员工程师,资格都很老。很多工人是转业兵,技术员又跟工人合不来,所以不好管。
设计处副处长史汝辑负责轿车设计,再往上,领导生产轿车总规划的是孟少农。庄群担任道路试验室主任后,开始搞轿车设计。怎么搞?首先要有样车。史汝楫和孟少农商量,要找两个主要样车参考,后来选了德国奔驰190和美国福特西姆卡。
我们参考美国福特标准,确定参照奔驰190发动机,西姆卡底盘,车身加以修改,试制了几台样车。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到1958年,大家夜以继日地干,根本没有休息概念,完成轿车设计试制和初步鉴定。
试验轿车性能方面主要有三:一是经济性,二是动力性,三是刹车性能。看是否舒适就要靠人来感觉,这些我很快就学会了。汽车技术性能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做,不然没有可比性。
到哪里做符合技术要求的鉴定试验?我们找来找去,在去吉林市的半路上有个岔路河镇,数公里外大概有一公里多的直线路,路面还不错,但比较荒凉。离这段路不远,有个福利院可住宿。
做试验时,我们住在福利院。不仅脏,蚊子也多,吃饭得跑到岔路河镇,很辛苦,但也没办法。除对路面有要求外,还要看天气,风速每秒不能超过两米,有风时也不能做,做一次试验要花很多时间精力。
所以,做成一件事情往往有许多因素,少一个环节都不行。不是一个人的力量,都是大众的功劳,
轿车试制出来后,有一天,清华大学教授宋镜灜正好到一汽。孟少农陪他到设计处参观轿车,宋问,轿车取名什么?
孟厂长说,正在考虑。
宋教授说,毛主席说过“东风压倒西风”,就叫东风好了。
孟厂长接受了建议,经一汽厂委会通过后,取名东风牌小轿车,送到北京去报捷,这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毛主席乘坐东风小轿车的消息。
正当我们要根据试验结果解决东风轿车存在的问题时,我们听到消息,中央要求制造高级轿车,供中央领导乘坐,而且北京准备接受这个任务。但一汽认为,既然我们有制造东风轿车的经验,造高级轿车也不在话下。
在大跃进形势下,一汽群情激昂,厂领导也同意做高级轿车,并取名红旗。红旗轿车试制出来后,因为能力有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两者取其一,最后确定舍东风而做红旗,东风轿车也就昙花一现。
我参加了东风轿车的选型和鉴定试验,也部分参与红旗轿车的鉴定试验。后来红旗轿车另立门户,离开设计处,我就没再参加红旗轿车的试验经历。
舍东风,孟少农不赞成。他话中有话,他说,卡车是小学生水平,轿车是大学生水平,我们小学生还没毕业,就要做大学生。
建国10周年,我们把试制出的红旗轿车带到北京,当时红旗轿车还没正式生产,仅仅是把样车送给中央领导看,样车跟产品车是两码事。
说实话,我很怀念东风轿车严格按照科学设计程序推进的过程。如果东风轿车能成功生产,一汽的历史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历史不能假设,这就是规律。
第一条试验跑道
一汽由苏联援建,苏联在国内没有建试验场,因此建一汽时也没有试验场项目。计划经济时期,项目计划里没有试验场,我们就拿不到建设经费。
没钱怎么办?早在造东风轿车时,孟少农找到何赐文和庄群一起筹备建汽车试验场。他们决定在一汽附近找地段自己建,前后找了好几个地方,有时也带我一起去考察。
后来在一汽西边(现在的东风大街)找到一个已废的加工厂。加工厂原来属于一汽,后来变成居民平房。这条路不平,不算太好,但因经费有限,孟少农决定在这里建试验跑道(testruck)。
所谓试验跑道,就是只能做某部分性能试验。能做所有验证试验的才叫试验场,试验场我们做不了。即使这样,这也是中国第一条试验跑道。
这条跑道比二汽建的试验场早得多。二汽当时有很多争议,有人问花那么多钱去建一个试验场到底有什么用?只有真正懂汽车试验的人才知道试验场的重要性。
二汽建试验场也是孟少农到二汽任职后的建议,孟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二汽确定建后,又搁置了一段时间,原因是土质(膨胀土)问题,遭到上级反对。但孟少农一直坚持,黄正夏(曾任二汽厂长)也坚持,最后才被批准。
孟少农设计出一汽试验跑道后,他想到一个最省钱的办法:利用一汽的剩余能力来建,可以不花国家的钱。比如一汽运输处出几辆车,让设计处出司机,由基建处施工队施工,找长春市政处做土建设计。
1959年底开始干,1960年初建成,试验跑道长5公里。可以说,如果没有孟少农,这条跑道根本不会建起来。所以我很敬佩他,从那时我才认识到,汽车厂必须要有自己的试验场。
也可以说,中国的汽车试验场是孟少农首创。有了一汽试验场的设想,才有后来各个试验场的诞生。
试验场设计期间也出过问题。我们原本按照苏联试验规范,路面平直度控制在千分之三以内,即1000米距离抬高不能超过3米。但这条路上正好有个洼地,要填平成本就得提高,实在拿不出钱,结果就超过了千分之三。
但这个千分之三数字本身是错误的,正确的试验结果应该是汽车往返试验的误差不能超过5%。打个比方,以结果是100为例,往返不能超过105~95范围,这样试验结果才可信。我们做试验时,来回结果都超过7%以上,因此这条跑道不能用于性能试验。
从这方面看,我们是失败的。但除性能试验外,其他测试都能用。
后来钱还是不够,就去找老汽研——从北京搬到长春的汽车研究所(合并前称老汽研,后来跟设计处合并,叫汽研所)。那是1960年初,陈全处长去找老汽研主任,希望对方出些钱来建。试验跑道建成后,老汽研、质量处、设计处都可共用。
中间还有段小插曲。试验跑道修好后,相当于给农村修了一条路,农民看到有马路,都往这边走。老汽研不满意,我们也不满意,但路也没办法封闭,要封闭又得花钱。
1962年,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到一汽蹲点。我们跟他反映这个问题,段部长就批评设计处。他说,你们没钱,不能自己动手封闭吗?后来我们弄些大石头垒起来,但也不能完全封闭,只能封闭农村的出口。
这样到了1965年,我们攒下些钱,想改造试验跑道,便于做快速试验。什么是快速试验?汽车要跑2.5万公里才能判定可靠性的好坏,要完成这个试验需要很长时间,也等不及。于是考虑怎么集中起来在一个区域跑,既能达到试验效果,又能省钱省时间。
道路试验室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结果文化大革命开始,打乱了所有计划。这时孟少农已调到陕汽,庄群被派到海南,要跟苏联合建一个试验站。道路试验室的计划落空。
军代表进驻一汽后,合并设计处和工艺处成立科技部。我们这些科长都靠边站,基本不上班,上班也没事干,每天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持续了两三年。
1969年底,我被下放到总装配厂当工人。做什么?汽车下线后检查,把不合格的零件换掉,我就做换零件工作的修配工。工资和级别都没变,还是科长。
我在试验室时跟总装配司机关系不错,工人们对我很照顾。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我喜欢当工人,没有太多思想包袱,就是干活。总装配实行三班倒: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晚上12点到早上8点。
我干了一年多修配工,接着被派去当检查员,就比较轻松了。
1972年底,形势基本稳定,陈全和庄群回到设计处,但实际掌权者还是军代表。上面让我回设计处,我不愿意。我去找总装配车间书记,我说,你要我,我就继续在这里干。接着又去找干部处,说总装配想留我,我不想回。
干部处处长说,这是厂领导、厂党委的决定。要改变必须向厂党委汇报,重新开会讨论。没办法,我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回设计处时,军代表正好去北京学习。我跟陈全说,我不想当领导,当个工程师或者技术员都可以。
陈全说,等军代表回来再安排工作。
趁这个机会,我申请休假一个月,回北京探亲。我父母于1962年回到北京,帮我妹妹照看孩子。
休假回来,军代表说科技部下面要设一个大试验室,总共有一两百人,包括道路试验室、发动机试验室、底盘试验室、车身试验室、电器试验室等。大试验室主任是李昌群,让我当副主任。李昌群原是试制车间的一般干部,中专毕业,出身较好,后来升任总厂调度室主任。
1973年军代表撤退,陈全和庄群重新掌权。我提议不要搞大试验室,让各试验室回归,我也回道路试验室。设计处领导讨论后表示同意,这样设计处又恢复原来机构。
一天解决十年遗留问题
回试验室后我就专心搞道路试验,着手解决原来考虑过但没解决的问题。比如快速试验,发动大家去找能做快速试验的样板路段,把500米路段按25厘米宽分成5条路,定一个定点,每隔25米用水平仪测试高低点,5条路就有几百个数据。坑洼高低都用水平仪测量,这就测了几千个数据。
数据怎么用?我们参考英国MIRA试验场,其中有条比利时路,由方块砖筑成,时间长后变得凹凸不平,这条路被移到试验场里面。假如按照汽车30英里/小时速度,在这条路上跑300英里就能确定可靠性。
但我们的数据没有根据。一位吉林大学数学系老师告诉我,在数学上这叫路面谱,可用计算机做一个随机路面谱,把数据导入得出谱值,再据此修路去做人工测试。冬天可在厂里用砖头铺路,一结冰就变硬,看看汽车在上面跑时人的感觉。
几个人分别去测试,试过好多地方,就凭感觉和经验,因为没有仪器测,也没其他参考资料。那时计算机有一个房间那么大,只有吉林大学数学系才有,所以要算数据,只能去吉林大学,过几天再去问结果,过程挺艰难。
从1973年到1977年,我们花了近3年时间才弄清楚该用的路面谱值。1978年初,我们确定建一条试验跑道,专门用来做可靠性试验,之前那条试验道路就不再用了。
1978年,李刚担任一汽总工程师后,让我们移地再建试验跑道。要把试验场移地,我回设计处时就听说过,其实早在1973年,我们就有意识再找一个可建试验场的地方。
这时老汽研根据我们研究快速试验路的结果,派很多人到海南试验站找地建可靠性道路。他们找到的那块地属于当地生产队,10吨以内的载重车都可以用。我们派王秉刚和王湘海参加,王秉刚是我的接班人,他们在研究可靠性道路时出过大力气。
1978年我第一次去海南考察建可靠性试验路的情况。刚来两个礼拜,对海南情况稍微有些熟悉,就被徐兴尧一个电报给叫回去,让我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

一汽派出19人代表团去日本。我匆匆忙忙学了一个月日语,就硬着头皮去。在日本先参观卡车厂和轻型车厂一个月,然后是三菱、五十铃、日野、日产和丰田。一个厂一个月,加起来正好半年,180天。
收获很大。我主要看试验场,日本有大大小小试验场20多个,其中四分之三我都看过。
丰田有个试验场建在山顶上,把山顶铲平后建试验场。我一看图片,觉得奇怪,就想去看。丰田方面说,那里没什么,不必要去看,给你放放录像就可以了。
我就将他军。我说,前面这些试验场我都看过,这个试验场建在山上,不知是真还是假?接待愣住了,经过请示,同意我、日方一个工程师和翻译3个人去看。
这是一个变速箱厂的试验跑道,变速箱和转向机为丰田生产。我问他们,建在山顶上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们说,防水问题。
在山顶上怎么防水?水又不会淹到。我又问。
下雨后,水冲下来路面全给破坏了。对方答。
为什么要在这里建快速试验路?对方说,变速箱在非洲某些个地方上坡时坏掉了,他们派技术员到非洲,把当地路面情况测下来移到这里做研究。
我很佩服日本人的这种精神和作风。我向丰田方面要求,能不能把试验场的路面不平度资料给我们?对方或许觉得,给你能有什么用?于是就给我了。我的想法是,拿这些数据回来研究路面谱,看看日本的跟我们研究的结果有什么不一样。

从日本回国后,我们一直在找能建更大试验场的地方。如果从1973年算起,前后花了近10年时间,到1983年还没找好。
我们选的地方吉林省不批。我去过内蒙古乌兰浩特,告诉他们一汽要建试验场。他们带我到离乌兰浩特一两百公里的地方,有个日本人废弃的飞机场,那里三面环山,一面出口。冬天山上下着雪,下面的草还是绿的。
我给一汽做汇报后,很多厂领导都去看过。他们认为地方很好,但是太远,离一汽有500多公里,运输各方面都不方便,就给否定了。
吉林省委书记赵修到一汽视察,一汽总设计师刘传经抱怨说:我们在吉林找不到地方建试验场。赵修便告诉吉林省副省长,让他批个地方给一汽。
过了10来天,副省长真来电话,要找一汽厂长黄兆銮。
黄兆銮通知我一起去找地方。我看过那么多地方,哪里最合适也说不清楚。但我灵机一动,冒险说出最近的地方,在农安县烧锅镇。
我们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去看地,约11个局级干部陪着副省长,包括公安局长、农业局长,以及一汽副厂长等。到烧锅镇后,副省长一看,地方挺好,空旷没人,差不多有100公顷,是公社养羊养马之地,不种庄稼。
副省长跟陪同的县长说,你们就支援支援一汽吧。既然副省长都发话了,县长只能表示同意。我们赶紧回去写报告,趁副省长出差前做完审批,一天就解决了10年都没解决的问题。
找地10年,施工10年
接着做试验场的设计,黄兆銮和李刚的意见是让一汽基建处承包。基建处不懂汽车试验技术,处长交给基建技术科负责,但把土填平后,技术科也说干不了。
试验场最难的是跑道弯道部分,我们考虑怎么办?刚好有个日本人,他是日本遗孤,在中国长大,当过一汽底盘车间调度员,对一汽很有感情。经他牵线,找到日本铺道公司承担。
日本人相当于中介,他让铺道公司请日本自动车研究所出面联系我们。日本自动车研究所和铺道公司合作,前者做担保,后者接任务,然后跟我们谈建试验场。
本来是很好的事,谁知道又出现一些问题。铺道公司到一汽谈判,带了很多人,有律师,有财务和技术人员,我们这边有厂长,有助理参加。
谈到最后,变成两个谈判组。一组属于技术组,由我和王秉刚负责;一组是财务和行政组。谈了两天,对方技术组认为一汽要求太苛刻,钱还压得这么低,他们干不了。
我们决定先谈技术问题,由他们设计高速跑道,施工以后再谈,这样只谈设计费用,大家都可接受。但一汽一位厂领导说,干脆跟他们谈个大合同吧。
这方面我有过教训。以前搞风洞就半途而废,见头不见尾,摸着头谈谈,最后没尾巴。因此我说,不能这样,我们还是分两段,第一段搞设计,第二段施工。
高速跑道设计很复杂,环形弯道不打方向盘,速度要保持自然,计算要精准。中国还没人做过,但有人去日本铺道公司学习过。
对方要价很高,仅设计费就20万美元。施工更高,要好几百万美元。铺道公司给我一些资料,告诉我,这些都得用计算机控制,平度要在千分之一以内。弯道设计本身就很难,我们国家虽然也能设计,但没有经验。
黄兆銮(时任一汽厂长)同意把设计和施工分开谈。现场讨论时,我们表态说,施工问题以后再谈,但肯定请他们监工。意思是用我们自己的工人,他们做现场指导。
有关设计谈成后,钱没问题,人也没问题,条件都讲好:什么时候交图,什么时候审图。看起来事情都解决了,没想到又发生了意外。
大概是11月,在北京的一个宾馆,我和铺道公司的一位领导签订设计合同协议。第二年春节后,那位要一次谈大合同的厂领导突然告诉我,厂里没钱,要取消合同。
取消合同就要赔钱给对方。我跟一汽领导沟通,我说,现在要取消合同,起码得赔付10万美元。何况对方已经开始干了,今年底就要出图。为什么要白白送人家10万美元呢?
我问厂里能出多少钱?厂领导说,赔10万美元还出得起。那好,还差10万美元。我去找中汽公司科技部的詹同震,他是詹天佑的孙子,我们关系不错,后面建海南试验场跟他也有关。
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借我们10万美元?
干嘛?他问道。
我把整个过程讲给他听。后来他终于说,行。
他跟胡亮局长商量后,决定提前把10万美元给汽研所,本来要到年底才给。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们坚持把设计做完。
其实做设计时,我们已给日本人预留了一块住地,这个详细过程就不讲了。我们派人到日本去学怎么设计高速跑道,同时,上海市工程设计院有位工程师,名叫崔健球,他原来就参加过一汽扩建试验场工作,他也帮着我们审查日本铺道公司设计的高速跑道。
图纸确定后开始施工。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该请谁来做,就跟基建处商量,请来北京计划建筑设计院,他们跟日本铺道公司有联系,也派人到铺道公司学过。北京计划建筑设计院帮我们设计总图纸,而高速跑道的设计图纸,最终由我们和上海设计院确定。
项目前期一直是我牵头,施工找谁?我建议让外面的单位干。海南有个福建施工单位,能保质保量。他们先做试验场边跑道,质量还挺好。刚做完,管施工的基建处又不用他们,要自己施工。
我反对这样做。我说,这样不行,保证不了质量。我们宁可多花点钱,让外单位做。他们不保证质量,我们可以罚他,一汽基建部门不保证质量,我们罚谁?但一汽厂领导认为资金不外流,结果让基建部门施工,质量一塌糊涂。几次返工重修,到1993年底我退休时,还没全部完成。

这样从1983年到1993年,我们找地10年,施工10年。一汽建试验场,全国第一个先干,我们的资料还被其他企业拿去学习。一直到1993年,返工再修,又返工,质量最差,完成得最晚。
日本汽车研究所一位副所长跟我关系不错,提供过很多资料给我。他曾问我,什么时候到一汽参观参观?我就推托自己已退休,不再管事,不知道具体情况。因为实在没办法让他们来看。
海南试验场
一汽建成的第一个试验场在海南。海南试验场从1978年开始,先做可靠性试验跑道,那时还叫试验站。文革期间,老汽研因离得太远,管不了,1972年一机部便交给旗下广州电器研究所代管。
广州电器研究所主要做电器,这一管就管了11年,搞了好几个电器试验室、电器楼什么的。因此,海南试验站里电器所占了多半。
到1983年时,中汽公司就跟一机部提出,汽车要发展,海南试验站再让电器所管不合适,应交给汽车部门管。一机部同意让汽研所(当时老汽研已与一汽设计处合并为一汽汽研所)派人到广州跟电器所谈判。
派谁去?汽研所当时管试验的是我。我就和詹同震、杨时平作为一汽汽研所和中汽公司的代表,去跟电器所谈判。
中汽公司担心我们三人比较年轻,对海南不熟悉,又找了赵尔承同去。赵是最初建海南站时的老站长,当时是重庆研究所副所长,70岁左右,已退休,中汽公司请他当顾问。
11年来,电器所在海南试验站建了很多房子。试验站无偿划拨给电器所管,现在要回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房子怎么处理就成为难题。
我们和赵尔承意见统一,意思是无偿给你,你也无偿给我。具体怎么分?最多把几间房子给他们,其他全部留给我们,试验站归我们管。
但电器所不干,他们非要划线,各分各的。划线主要问题在主楼,主楼是木石建筑,是最好的房子,代表海南站样板,到海南站的人基本都住在那里。
我们连谈两次,1982年、1983年各谈一次。回来后向上汇报,再去谈,双方各提出一个方案,都谈不到一起,最后不欢而散。
他们的想法也简单,这11年来国家没拨过钱给海南站,都是拨给电器所的,电器所用自己的钱来建海南站,现在海南站要拿回去,就得把钱赔给他们。我们当然不同意赔。
谈到1983年四五月,一机部下死命令,从计划司、技术司派出两个代表。那边是机电局,这边是中汽公司,再加上技术司和计划司一起谈判,一定要谈出结果来。
汽研所还找来陈全当顾问。陈是海南铁矿第一任矿长,两年后调回北京,又调往长春,对海南情况比较了解。
谈来谈去还是谈不拢。我就跟其他几人商量怎么办?海南站一位工程师对我讲,现在主要问题是主楼,站里面建有电器试验室楼,要把电器楼跟主楼划开,怎么划都划不清。
最后没办法,我们让步:主楼给电器所,电器试验室楼给我们,相当于把试验场分成了两半。
电气所占驻海南站,电器试验没多少活可干,没有汽车试验其实挺亏本。主要是机械部机电局局长想电器所在海南有个落脚地,所以不想放弃。
1983年5月1日双方签字,我跟电器所所长做交接。
海南试验站归汽研所管后,我当试验站站长。试验站没钱,汽研所拨来几万块钱,作为一年运营费用。
这时赵尔承说,他对海南站挺有感情,想把这里好好管。汽研所就聘请赵尔承当党委书记兼副站长。
我要管一汽试验室,不可能长期住在海南。于是就跟汽研所讲好,半年在海南,半年在长春。这就苦了赵尔承,他一直守在那里。
1983年底,耿昭杰(时任一汽厂长)到海南,对管理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派来赖国平。赖也是印尼归侨,比我大两岁,原来在一汽搞电机,到长春市当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又回到一汽。他担任海南站第一副站长,赵尔承是书记,我是站长。
1984年底,赖国平熟悉海南情况后,赵尔承身体不太好,要求退休,介绍一位工程师许涛。1958年建海南站时许涛就在,当时已退休,就把他请到海南站管技术。赵尔承回重庆老家。
我也不再当站长,全交给赖国平管。但我在汽研所还管长春试验场和海南试验场。
海南站困难很多。举个例子,海南站试验场不是一块整地,这边一个生产队,那边一个生产队,有五六个生产队。跟生产队订合同,以什么为界只能在文字上说明,没有地图。
当初海南站的领导跟生产队签合同时说,我只要这块地,你们可自由出入。但要搞试验场就一定要封闭起来,而要封闭,首先要把地界搞清楚。
这就苦了赵尔承和赖国平。我只在海南待半年,跟他们研究怎么定地界。定完地界后,我回长春,他们继续负责与生产队谈判。
我们的打算是,先把地桩做起来,再做围墙。做围墙问题就更多,原来让他们通行,现在又不让通行。怎么办?找到县政府,县政府出面搓和,给他们一些补偿,让他们绕道走。
建围墙时,不光涉及修围墙费用,还有赔偿农民绕道的费用。钱紧张时,就跟赖国平商量,找一汽副厂长沈永言支持。沈当时在一汽管基建,问我们需要多少钱?后来让曹建拨来60万元基建费。
围墙建完后,因为跟农民谈判问题很多,两三年后围墙才全封闭。
接下来建高速跑道。我们先找上海设计院做设计,他们拿来我们与铺道公司的图纸做参考,设计很顺利。后经县政府推荐,找福建队施工。沈永言亲自派监工人员,他起到很大作用。
施工全部完成时,我已退居二线,由王秉刚接管海南站工作。
到底谁先建成试验场?二汽虽然开工比我们晚,但建得比我们快。一汽看二汽试验场要建起来了,就抓紧海南站施工,最后比二汽早半年建成。所以,第一个试验场是海南试验场,第二个是东风(二汽)试验场,第三个是总后勤部试验场,在安徽定远县。

总结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十多年,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我主要主持了三项与汽车试验有关的事:一是长春汽车试验场的建设;二是海南湿热带汽车试验场的建设;三是中国汽车质量检测中心的建设。
这三个项目其实都是为汽车整车质量鉴定服务,应该说都没有离开过整车试验。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在一汽干了41年。我这辈子做的事情很多都是见头不见尾,长春汽车试验场后来由王秉刚与孟祥符负责,怎么建成的我也不清楚了。